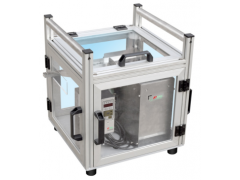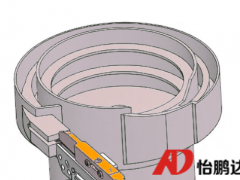隨著我們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,創新,尤其是科學與技術的創新被提到幾乎是最高的位置。
這樣做的必要性可以從國家的科學發展報告里得到印證。首先,科技創新是后發國家最重要的事情。韓國在五十年代比中國要窮,日本當時跟中國的GDP 差不多,年人均大概在90 多美元,而韓國只有它的2/3。但是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,韓國今天已經達到 3 萬美元。美國作為世界的標桿是 5 萬多美元,臺灣大概是 2 萬多,香港 3 萬多。而我們大陸今年可能到八九千,北上廣深肯定是超過 1 萬。這些當然只是從數字上看。除了韓國,正面的例子還有芬蘭。在上世紀80 年代,及時把握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機遇,大力發展通訊產業,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。也有一些國家成為反面的教訓,像拉丁美洲,阿根廷、墨西哥等等。尤其是阿根廷,在 50 年前非常富裕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建筑絕對不比上海的要差。他們到達過1 萬多美元的人均 GDP, 但是現在退到了 1 萬以下。墨西哥也曾經到達了 1 萬,又退到了幾千,然后再慢慢的爬回去。這就是因為他們只靠本國的資源優勢,包括勞動力。這些都是要過時的。但同時過度依賴外國資本和技術,忽視自主創新。當然他們也試圖創新,花了很多錢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國立大學。27 萬學生,就像一個城市。然而并沒有達到目的。
在“2007 年科學發展報告”中也提到,我國的關鍵技術自給率比較低。各位可以到大公司去看看,差不多都是進口的。尤其是高端的設備幾乎沒有一樣不是進口的。發明專利總量 2007 年排名世界第 8 位。現在好一些了。論文總數現在已經排到了第二位。引用頻次也有提高。
但最關鍵的還不是這些數字,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原創率。我們的論文大多數都是“炒菜”型的。人家發現了這個菜,我們去加點鹽,放點油,然后再炒一次,并不是原創型的。從這個角度來講,所有領域的開創性的東西還都是在國外。國內的絕大部分還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,就是換油換鹽,或者把兩盆菜放在一起再炒一次。
因此,我們希望探討一下別人做科研創新時所遵從的一些基本原則,也就是所謂四條基本原則。這個是在九十年代,美國科學促進會召集了一批諾貝爾獎級精英總結出來的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第一是要“結合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”。這句話不是說說而已,這句話要真正做到非常困難。常常聽人講,“我是搞基礎的"。另外一個說“我是搞應用的”。做應用的人瞧不起基礎,做基礎的更瞧不起做應用的。這一切都是創新的障礙。一定要真正地結合。后面會通過舉例子讓大家看到,沒有一樣創新可以單獨只限在基礎研究方面。因為最基礎的那些東西包括物理化學早就基本做完了。甚至于生化的一些最基本的東西,DNA 等也都已經搞得很清楚了。但是,搞應用的人若不涉及基礎,就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炒菜,甚至于連炒菜都算不上。所以這一條極其重要,放在第一。
第二要“綜合各個領域”,這一句大家更是耳熟能詳了。怎么綜合呢?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希望大家能夠結成一個團隊,真正的去把各個領域融會貫通。但是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。尤其是作為領軍人物,要能夠跨領域跨行業,知道很多基礎都是相連相通的。這也跟我們的教育有關,長期以來被蘇聯的教育系統不止搞壞了一代人,甚至于到現在都還是如此。我們的大學名稱本身就是一個反例。國外的大學,凡是一個大學就是綜合性的。并沒有什么“海事大學”、“中醫大學”、“航空航天大學”。是大學就應該什么都有,而不是細分成各個領域。
第三是要有充沛的時間。充沛的時間不是說可以無限制地做下去,而是指不要有一個“催命”的時間表。從這個角度講,你按計劃做出來的東西不叫科學研究。計劃連經濟都不行,研究更不行。
第四是要超越常規。各位肯定深有體會,尤其是在國內條條框框太多,西方好一點,但還是需要經常地打破常規,才能做到科研創新。
所以這個四項基本原則在全世界任何地方,甚至在美國,都很難保證隨時隨地能實現。正因如此,創新就變得尤其難。我的意思是指真正的創新,不是炒菜。尤其是科研創新,那是難上加難。也正因為如此,你天天看的絕大部分論文,都是跟著人家后面。真正的創新,一眼望去,不管它發表在哪個雜志,放在什么地方,是個人都能看得出來。
這幾條原則還須稍微詳細地作些討論,要用一些具體的例子作說明。
第一是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。這就先要問什么叫創新?創新首先是知識的創新。不是說人家有了原子彈,我也想方設法去造了個原子彈,這個不叫創新。雖然很傷感情,但是我們要把道理搞明白。知識的創新才是真正的創新。沒有新的知識就沒有超越常規的新應用。這里的一個正面的例子是高溫超導的發現。高溫超導在1987年一下子轟動了全世界。現在大家都知道高溫超導已經很成熟了,甚至于變成了一個產業。高溫超導很快就得了諾貝爾獎。高溫超導是在陶瓷系統里面發現的。大家讀中學時就知道陶瓷是個絕緣體,高壓電線都用陶瓷相隔。既然是個絕緣體,連普通導電都談不上,怎么想到做超導呢?原因就是,歐美的本科是一個通才教育,他們的知識面相當的廣。做出這個科研創新的兩人是在瑞士的IBM, 他們又沒有任何常規的任務,就扯到了陶瓷上面。當然中間是經過了很長的過程。這個例子給整個科學界非常大的震撼。那么多人搞超導,搞來搞去才 20 幾度。在合金上面拼命地炒菜,炒了近 70 年沒有大的進展,最高溫度只到了 23 度。而他們那個系統一下子被后人發揚光大到了液氮的溫度,就是七十七度。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正面例子,科研創新的最重要的例子之一。從原本絕緣的材料到發現它的高溫超導特性,需要對各個學科和領域都有所了解。尤其重要的是,要跨越“基礎”與“應用”之間的鴻溝。如果只是局限在“基礎”或者“應用”之內,是無法打破這個思維局限,取得這個重大突破的。
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反的例子。新加坡從高中開始,學物理的人不學數學跟化學,學化學的人不讀物理和數學,學數學的人不做物理跟化學。結果到了大學的工學院,數學就只是高中的水準,連微分方程都沒法做。90 年代他們從美國請了一個新加坡人回去當了他們的大學校長,徹底改變這一切,才讓國立大學在這短短幾年的時間內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大學。什么東西都按美國的,把新加坡的那一套徹底改變。但是他們細分的科目就跟國內一樣,已經根深蒂固。隔行如山,很難在一代人里面把它徹底消除。
第二個是要綜合各個領域,各個領域要學科交叉。這里面尤其要強調的是數學物理這些基礎。因為你沒有辦法,在各個部門分得很細,每人只知道自己眼下的一畝三分地的情況下,做到綜合各個領域。在國外這個事情相對容易一些,因為一個大學的校園里面,很多時候是你的隔壁就有別的領域的專家。像我們一個樓里面有各種系的教授,就讓你們混合在一起。而不是說某某系全在這一棟樓里面。我在哥倫比亞的時候,整個工學院就是一棟樓。若有問題,坐電梯就可以到另外一個什么系得到解決。這個就是一種學科交叉,大家可以打破門戶之見,隨時可以交流。
第三是充沛的時間。新發現往往需要非常長的時間,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時候能發現。假如可以設置詳細的時間表,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新發現。這里有個很好的例子,就是二戰當中磁控管的發明。大家知道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國才全身投入戰爭。當時日本的艦隊快到了眼前,美國才發現。怎么回事呢?當時的雷達是用長波的,稍微小一點的東西, 就“看”不見。其實不光是美國,英國德國都希望把雷達波長改短。雷達的原理在一戰的時候就已經知道。但是因為當時的真空管里面電子來回需要較長時間,所以它的頻率提不高。那怎么把電子管的頻率提高,使得不要等飛機到了頭頂才發現呢?小羅斯福總統把這個重大項目交給了麻省理工學院,成立了聲名赫赫的"輻射實驗室”。因此麻省理工學院就變得很“牛”。他們先是拍胸脯說幾個月就能解決問題,但搞了一年多還沒有解決問題。這就是之前說的,真正的新發現不可能有時間表。但與此同時在英國,在德國飛機的轟炸下,有兩個科學家在防空潤里面居然做出了可以產生高頻率的電子管。因為他們發現引入磁場以后,可以做到高頻。總而言之,“有心栽花花不開,無心插柳柳成蔭"。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這也就是為什么大學要實行終身教授制。你要讓他有個保障,不要去催他,要給他充分的信任,要“養”著他。這些大學教授才會有可能做出真正的科研創新。除了少數的"爛蘋果”,大部分人是不會讓大家失望的。
剛到麥克馬斯特大學的時候,我們的教務長是哈佛的畢業生。曾說起當年, 哈佛大學招了一個年輕的助理教授。他干了近 30 年,居然沒有寫一篇文章。要是在麥克馬斯特大學早就踢出去了,終身職肯定拿不到。但哈佛就有這個雅量讓他繼續做。等到了第 31 年的時候,終于出了一本書。而且很薄的一本書。從此以后,凡要研究這個方面的人,都得先讀他這本書,這成了該領域的“圣經”。大家應該也聽說過美麗心靈這個電影,講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約翰·納什的故事。哈佛和普林斯頓就有這樣的雅量和耐心。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可以成為世界的頂尖學府。
第四個原則,超越常規。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話題。我想根據基金申請當中的問題來談,因為我在美國加拿大都曾參與了這方面的工作。美國最健康,加拿大稍微差一點。歐盟我也曾有機會觀察過。我要談的是,你要能隨時調整方向。就是說你拿了錢,去做 A 問題,也就是你打算在A 上面發些論文。結果你做著做著發現,得到的結果不是 A, 而是 B 甚至于是 C。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把你的方向調整過來。你的科學問題,必須改成 B 甚至于改成 C。這個時候你對科學的貢獻其實要比你盯著 A 要大得多。給經費的人就應該有這個雅量讓你去做 B 或者 C, 甚至要鼓勵你去這樣做。
前述這四項基本原則,其實是西方大部分科學家的共識。但似乎很少公開宣傳,因為大家覺得這些是不言而喻,當然也有可能被認為是“武林秘籍”不可輕易示人。
圖說智能化網新域名:http://www.zcdqw.com.cn/